当“天下”遇上“世界”——读《黑龙江纪事:内河·界河·掐头去尾的大河》
文/戴时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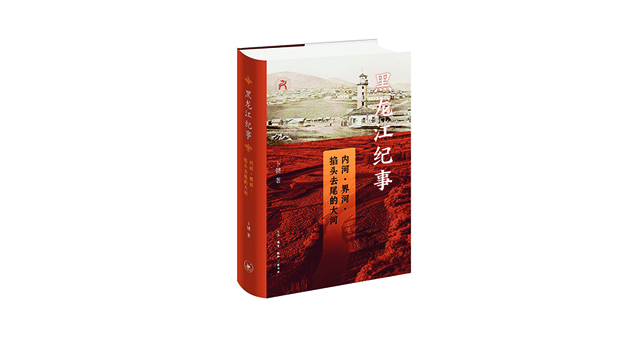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就演变模式而言,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从先秦到晚清,是在一个“超稳定结构”里得意洋洋地自我复制;从晚清到当代,是在一个“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中进退失据地应对挑战——在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与外国的对决,也是不同时代的对决,更是“天下”与“世界”两种观念的对决。
近代中国有几大痛心之事,使国人至今难以释怀:一是鸦片战争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失去了香港,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一是咸丰八年(1858),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一是在甲午海战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两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一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其中,“最痛的点就在黑龙江流域”。
卜键的《黑龙江纪事:内河·界河·掐头去尾的大河》,以丰富的历史内容(全书约50万字)、完整的叙事结构(正文分为21章151节)、严谨的学术态度(全书援引成书的史料90种、中文著作58种、外文译著58种,各章文末共有注释718条),讲述的就是当“天下”遇上“世界”时,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这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前世今生,以及与此相关的各色人等之间的恩恩怨怨。
自己祖籍海南琼海,生在广西贺州,对书中提到的南人北上,自然比较关注。心里总是在想:这些前辈千里之行,究竟所为何来?《黑龙江纪事》告诉我们:福建水师的陈枚还率领一支擅长水上作战的家乡子弟兵,从温暖湿润的福建艰苦跋涉,来到冰雪覆盖、人生地不熟的爱辉,为的就是收复故土、戍守边疆。既然身为军人,自当保家卫国。“家国情怀”大约是后人对他们的赞誉,他们自己可能未必会有更多的想法,但这并不应该也不会减少后人对他们牺牲精神的敬重。
在选材上,《黑龙江纪事》是一曲白山黑水间的“凡人歌”。倒也不是没有名人,不过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原住民、外放的官吏、从闽南北上的普通士兵、流放的文人、闯关东者,加上俄罗斯的哥萨克、沙皇的特使、身兼多种身份的科学家、到远东淘金的探险家、十二月党人及后裔,以及日本间谍、英法海军、后世的史学家与作家……不管他们各自追求的是什么,也无论他们是自觉行为还是被动参与,这些人都构成了“黑龙江纪事”的主角,共同演绎着历史场景里的风霜雨雪和现实生活中的爱恨情仇。
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则是自诩“中华统绪不绝于缕”的大清帝国与对标西方文明的沙皇俄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对决。这种对决的非对称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历史演变的全过程,令后人痛心而又无奈。
我们看到两个朝廷对时代挑战“同”中有“异”的解读。在作者看来,那是一个蒙昧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变革之声渐起的时代。面对同样的严峻挑战,两个朝廷依据各自的理解,做出不同的回应。仅就外交思路与话语模式、君臣关系、人才使用等方面而言,两国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中的“道道”值得玩味。
我们看到既无实力又无技巧的外交。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理念,大清的统治者只知“天下”而不晓“世界”,对于近代以来“外交谈判”的基本理念、规则意识、制度设计、团队建设、谈判技巧、经验积累等重要事项,更是一概不知,甚至好像也不想知道。面对狡猾的沙俄君臣,大清只能屡屡败下阵来。
我们看到“道”与“器”均不如人的军事。庞大的清军看似所向披靡,实则每一仗都打得颇为艰难,取胜后即忙于庆功与虚假宣传,并不知总结改进。其实,就是在所谓盛世,清军在军事思想、人员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西方的差距也日渐加大。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和反映,中俄军事上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制度差异的必然结果。
我们看到滞后的视野与认知。欧洲经历了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列强竞起,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亦非昔日可比,而置身于世界大变局之外、缺少国际视野的大清君臣,却依然以蛮夷视之。对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作者认为虽然这句话曾广受夸赞追捧,实则仍然充溢着“天朝”观念,缺乏开放胸襟和外交诚意,对国家与军队的变革没有根本性效用。晚清的朝廷和封疆大臣,看上去既不缺心眼儿,也不缺少对外国人的警觉戒备,但是却缺少对军事革新和国际格局的了解,也缺少国家之间应有的坦诚和大智慧。而令今天的读者感觉尤为突出的,就是书中的“天下之主”缺乏对“天下事物”的深刻理解和强烈担当。
大清与沙俄之间的这种比较,似乎并非作者有意而为,而是走笔到此不得不为之,不料却在无意间揭示出同为专制制度,两者究竟差在哪里:从最高统治阶级到普通士兵,从政治传统到行政理念,从科技进步到军事变革,从外交规则到官场习俗,从时代观念到全球意识,从宏观视野到细微末节……种种形式的“非对称性”无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持续而广泛的非对称性,导致在近代以来的中外对决中,大清帝国一败于英,二败于俄,三败于英法,四败于日,五败于八国联军……其恶果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黑龙江纪事》显示,由于历史因果关系复杂且诡异多变,也由于相关文献特别是中方文献的缺失,“大历史”中仍然存在不少缺环需要读者脑补。比如:1858年5月20日,如果清军能在大沽口的近岸之地多修建设有射击孔的暗堡,如果能将炮台修筑得再坚固一些;如果清廷能接受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或许并非出自善意但却仍然是有道理的建议;如果……那么,这场战争或许将是另外一种结局。而这不仅可能导致出现“黑龙江纪事”的另一个文本,甚至可能影响中国近代史的整个进程。
可惜,历史从来不会正视“如果”——它只是把命运多舛的故事、落满灰尘的史料、残酷无情的场景和不可抗拒的逻辑一股脑儿抛给后来者,然后转身离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名曾任爱辉高等小学校长的边瑾,在《龙沙吟》诗中写道:“龙沙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在今天的爱辉城里,有一座著名的历史陈列馆。在院内通向主楼的路旁草坪上,排列着大小不一的石块,石上以朱墨题写某某屯,一共有64个不同的屯名,代表着的就是那永难回归的“江东六十四屯”。
张杨在《夏威夷:帝国往事》一文中写道:1899年年底,梁启超来到已被吞并但尚未正式成为美国第五十州的夏威夷。因疫情滞留檀香山期间,他完成了流传后世感动无数国人的《少年中国说》。1900年1月,置身“新旧二世纪之界限,东西半球之中央”,梁启超感悟此乃“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于是写下壮阔的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而“心里怀想的依然是大洋西岸的‘老大帝国’和‘少年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异国他乡,写下对心中故土的期盼,以“少年中国”剑挑“老大帝国”——那分明是两种历史轨迹的对决,更是两种发展观念的对决。
历史就是当代,转瞬已近百廿。合上卜键的《黑龙江纪事》,耳边响起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今天的我,多想一步跨过那条原为中国的内河,后来屈辱地变成中俄的界河,最后沦为掐头去尾的悲怆大河的黑龙江,让“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为了时代风云变幻不停的脚步,为了两百年来难以实现的牵手,为了国人心头时时泣血的海棠。
(卜键,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出版学术著作19种。其著《黑龙江纪事:内河·界河·掐头去尾的大河》已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