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地的敬畏和感恩——《大地上的庄稼》赏读
文/潘志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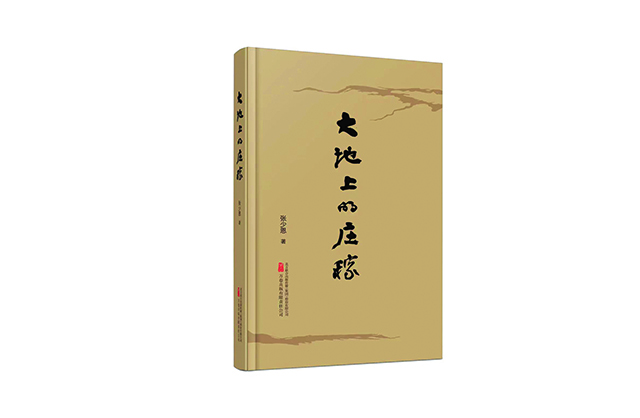
一本厚重、精致的散文诗集《大地上的庄稼》摆在我面前,作者张少恩。我怀着一颗歆慕的心赏读,很长一段时日,总算翻到了它的尾页,也密密麻麻地记下了许多精彩的诗句。我梳理我的印象,进行鉴别和斟酌,竟满脑子茫然,不知如何下笔。可心里一直攒动着两个概念:敬畏和感恩;它贯穿在诗文里,营造出浓郁的诗意,作者浸泡在这诗意的王国里,有着甜美的幸福。
敬畏是人们面对自然、生命、道德、法律等庄重对象时油然而生的一种情感,一种态度,一种觉悟。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常说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做人如此,创作也该如此。因为敬畏总能看见尘世里的善良,认清人生的方向,体悟到事物的价值;因为感恩总能涓涓于怀,时有所得,集腋成裘,收获满满。张少恩先生是敬畏和感恩的忠实践行者,也是敬畏和感恩的丰硕受益者,他总是小心翼翼,谦虚为人,活得坦然,活得通透,经行在多年散文诗的创作里,享受着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栖居的生活。
他的文字是有立据的,也构成了体系,往大里看,可以说形成了他特有的格局。在他的诗集里,庄稼、花卉、阳光、时令、大地、月夜、秋天、灯火、亲情……无不包容;所有这些,一进入他的视野,一到他的笔下,立即诗趣盎然,诗兴闪烁,仿佛他有一支生花妙笔,有一根点铁成金的手指。诗集分为7辑,140余章,汇聚了作者20多年的创作成果,洋洋大观。剔除外表的纷纭,往深层探究,还是那几个字:敬畏和感恩。
在我看来,敬畏和感恩本身就极具诗意,它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文字,不需要繁复的修辞,即便原汁原味的呈现,也照样耐人寻味。如“站在田头放眼丰收的人都与我沾亲带故,他们的额头比春天明亮”(《我与稻乡有血缘关系》)。作为60后,绝大部分人都是农二代,与农村和庄稼相处多年,至少童年青少年是在泥土里、庄稼丛中度过的;虽然后来大多离开了泥土和庄稼,但因为这段经历的缘故,他们中许多人一提起就怨苦连天,庆幸自己的逃离,若这样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写的了。还有一些人闭口不谈,任它埋没在记忆里,冻结在喉舌间。倘若态度一变,有敬畏和感恩之心,那段经历似乎就是金不换了。作者坦言“站在田头放眼丰收的人都与我沾亲带故”,再看他们的额头就不是布满皱纹,不是黝黑,而是明亮的闪光了,也有了“比春天明亮”的盛赞。如“一粒粮食是渺小的;一穗粮食也是渺小的。而一大片庄稼就举足轻重了。要是它辽阔、磅礴,翻卷金黄的稻浪,就不同凡响了”(《饱胀的天下粮仓》),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粮食,若没有敬畏和感恩,一粒是渺小,一穗是渺小,一片还是渺小,即便丰收了,卖不出什么好价钱,若谷贱伤农,更让人失望和怨艾。可到了作者眼里心中,却有“举足轻重和不同凡响”之誉,诗意在这两个词汇里萌生和漫溢。再如“丁香让我敬畏——深邃的赤紫,高贵的气息,精巧又细微的花瓣透出其卓异的思维”(《哦,丁香》),丁香虽然被古代诗人多次吟咏,显得神秘而经典,倘若真的遇见丁香时,可以说毫不出众,无论花形、花色、花香,都远不及牡丹、荷花、菊花、梅花等,可一敬畏就截然不同了。它的赤紫便有了“深邃”,香气便有了“高贵”,花瓣便有了“精巧和细微”,这些本已蕴藏诗意,加之“透出其卓异的思维”之语一出,就更添一份诗意了。
敬畏和感恩的着眼点在崇低,对生活中普通的、渺小的、有滴水之恩的事物,都能倾注青睐、关爱,真情描之,真心咏之,发掘它们的闪光,呈现由衷的景仰。在这一点上,作者表现得尤为踊跃,或者说已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深嵌的精神使命。他在《关注大地的细节》里直言“请俯下身子,关注大地的细节——具体而微的事”,亮明他的态度和旗帜。崇低故能以小见大,对于小小的蝴蝶能产生“那只蝴蝶翕动着翅膀,突突地发动”的奇想,幻生出“在辽阔大地上,它拖拽着暮色中巨大的货船”的能量。崇低能从普通中见出不普通、平凡中见出不平凡,深层挖掘出卑微事物蕴藏的内涵和价值,如人们生活里的灯火和夜色,大多数人已麻木和漠视,碰不出灵感的火花和情感的涟漪,可作者萦萦于怀,“在繁华的都市里,我并没有感到荣耀和自豪!越来越炽烈的灯火毁掉了夜的安谧,我能感受到夜的委屈和星空的沮丧”(《灯火辉煌的宏论我并不苟同》),又说“我爱的夜是萤火虫画下的浪漫的曲线,是虫鸣对倾听的拥趸。是草木香与寂静的相融,是梦的根深蒂固带来生命的强旺”,两相对照,一起一伏,褒贬分明,爱恨立显。
敬畏和感恩的终极是仰望和举高,彰显事物隐性的特征、被遮蔽的光芒。如果俯视或平视,就不容易发现,或被自己忽略,失去本该能深刻认知的机遇。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尘世之物总是仰望,将其举得高高,也每每心生灵犀,爆出惊人之语和令人艳羡的诗意。如“所有的花蕾都攥紧了拳头,暗语的眼神酝酿集体的暴动!春天来了,每一朵花都有开天辟地之力!”(《每一朵花都有开天辟地之力》),不说惊世骇俗,肯定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洗刷三观之功效;这样定义,我也觉得有点夸张,冷静品味,又深以为然。他高看暴风雨,写下“此时大雨视我为琴弦,悠悠弹拨。我穿行在风雨中,束缚已久的躯体获得了解放”(《暴风雨,我豪迈的披肩》),没有丝毫淋雨落汤鸡的狼狈,只见与苏子异曲同工的豁达和豪迈。他抬举芦苇,断言“一穗芦花是一个小宇宙,严密而柔软”(《对一穗芦花的探求》),不重复古人对芦花的感叹和忧愁,不囿于笛卡尔“人是一根思想的芦苇”的藩篱,一个“小宇宙”之喻,一个“严密而柔软”之描述,更显芦苇之大,也带给人一番崭新的思考。
敬畏和感恩能让文字得到源源不断的提炼和升华,进而走向诗意王国。作者敬畏土地,感恩庄稼,他说“大地有圣贤之气”(《田野仿佛完美的思想令人着迷》),说“稻子华丽转身,高贵的气质在一切草木之上”(《稻子高贵的气质在一切草木之上》),说“我知道弯下腰,撒出种子,大地就溢出甘美的风声”(《丰收的光芒是汗水荣耀的归来》),说“我热爱大地上的一草一木,对田野的气味更是情投意合”(《大地是装满天籁的吉他》),似乎有吐不完的吟唱,打不尽的美妙比方,让人跟着他的诗行着迷和痴迷。他敬畏阳光,把太阳的光芒落到实处,便有了“黄金的歌喉,黄金的舞蹈”的意象,“是盛世的庆典”的拔擢。他敬畏秋天和月光,说“秋天是献礼,是爱与思的收获,是大地的盛典,是耀眼的新人牵手”(《秋天不是阳光的磨损而是梦想的擦亮》),说“大地的果实血气方刚,在月光里散布甜美的芬芳。风为宁静的湖泊描眉打鬓,闪耀的星辰为秋天锦上添花”(《明月为光荣的秋天锦上添花》),他举重若轻,赋予秋天和月光以一幅幅绚烂的画卷。如果说题目是诗文的眼睛,这些眼睛皆含情脉脉,诗意绵绵,扫一眼便摄魂夺魄。他铭记父母之恩,写下《一盏灯火不断地向我发散人间的温暖》《父亲粗糙的大手分蘖精细的农业》《丰收的田野有父亲精彩的页面》《娘的大雪》《母亲不在,世界轻而空》等篇章,赋予亲情以醇厚的诗味,让人咀嚼之后,唇齿久久生香。
一般而言,敬畏和感恩都具有局限性。有人只敬畏崇高、伟大、神圣和英勇的事物,对其他事物若没有轻视和鄙视,就算是高看了;感恩也多限于亲情、朋友等有恩于己的人,相对狭隘。作者的敬畏则具有广泛性和超越性,大到天地日月亲情,小到一花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能敬而畏之,敬而颂之。一切有恩于他的,无论远的近的,大的小的,实的虚的,物质的精神的,都能拾取一一纳入诗文,发自肺腑的感激和铭记。因此他的敬畏和感恩显得自然和丰厚,常信手拈来,或水到渠成,或瓜熟蒂落。
厚重、精致是《大地上的庄稼》的物质部分,也是它的精神内里,这种和谐统一,得益于作者层出不穷的诗思和妙笔生花的文字。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少恩先生的敬畏和感恩,走的正是这条路径。他在自序里说“诗必须有自己的异响”“诗歌是对灵魂的关照”,又说“请拿出你的勇气和智慧,去刷新词语之传统的天空”,还有许多精粹之论,不再一一引述。在语言艺术方面,他特别擅长遣词,一个熟知的词汇、成语和典故,经他一拿捏,立刻焕发出新彩,扩充了外延,增添了不同的意境,也浓郁了蕴味。倘若能消除个别之处的牵强、片断化,而能深层融汇,浑然一体,就炉火纯青、别有一番天地了。他用“城市寄居蟹,乡愁领受人,文学痴心汉,诗歌朝圣者”为自己画像,几十年如一日,经行在人生的旅途,经行在自己的诗意王国,孜孜以求,也必将成为散文诗坛一抹独特的“异响”和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