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夫妇的家国情怀
我应邀赴日研究日本战后作家野间宏时,住在老朋友池田勇位于热海市东海岸町的温泉公寓。那里安静,空气好,离图书馆近,而且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应俱全,打开行李箱,就可以开始工作,极为方便。但没过几天,妻子对我说,日本的炒菜锅是平底的,很浅,用起来不顺手,稍不小心,菜和油就会溅出来,容易烫手,虽然努力适应,但几十年的积习难改,还是不习惯,所以想买个类似在北京用的深底铁锅。我陪她去了多家商店,都没找到。一打听,原来日本人炒菜都用这种平底锅,没办法,只好凑合着用。
一次与住在东京的徐前通电话闲聊,无意中说了买锅的事,她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深底锅,但记不清了,有空去找找,说不定能踅摸到。我说,你可拉倒吧,我何德何能,竟敢叫一位堂堂的文学博士、大学老师,满东京为我找锅,这不是小题大做,大材小用吗?她也笑着说,我本来就是专业主妇、业余博士。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她从东京寄来的快件,里面有日本产的北京铁锅(实际上是大马勺),还有锅盖、擦锅灶油污的专用纸等日用杂物。
徐前、黄华珍两口子,是我以前的同事、文友,算起来,已经相识四十多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劳动锻炼的农场分配到某图书进出口公司亚洲处日本科时,黄华珍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他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华侨,细高个儿,头发自然卷,衣着整洁,文质彬彬,话语不多,听说印尼文和英文都不错。当时物资匮乏,生活单调,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每天下班后,许多年轻人无所事事,用打牌下棋钓鱼消磨时间。但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见不到小黄,他喜欢读书,总是在办公室或宿舍捧着一本书,沉潜其中,读得津津有味。

夫妻重访五十年前徐前插队的东北大草原
徐前大约比我晚来三四年。她是北京知青,到东北插队,表现突出,被推荐到北京外语学院学日语,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她很腼腆,不爱说话,开会也不吱声,躲在人后,悄悄地坐着,有时领导点名叫她发言,她话没出口,脸就红了。那时机关经常办黑板报、壁报,她的文章卓尔不群,文采斐然,在年轻人中不胫而走,小有“文名”。我们交谈不多,只记得她生在一个兄弟姊妹很多、又都很有出息的大家庭,老祖母八十多岁,身手矫健,能上树打枣!我们开玩笑说,从未见你伤风感冒,原来是祖上传的,基因好。
那时有机关干部自带干粮、下乡义务劳动的制度,名为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当时,大家都二三十岁,血气方刚,争强好胜。记得有一次到郊区割麦子,人人“铆”足了劲,想比试一番,争个高低。我在农场劳动两年,割过稻子,虽说不上行家里手,但弄个中上游大概没有问题。谁想到,比赛一开始,徐前就一马当先,没多大工夫,就把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甩下了十来米。我们不服气,不断磨刀,狂呼乱叫,拼命追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汗如雨下。还有个傻哥们儿,手忙脚乱,把脚砍出了血。快到晌午时,天气越发闷热,大家看根本不可能追上,都泄了气,于是偃旗息鼓,躺在麦梱上抽烟喝水吃干粮,还顺便给徐前起了个外号“飞刀徐”。但这个外号只在内部流传,没有公开,因为它使我们想起麦田中的耻辱、惨败、丢人现眼。

与恩师石川忠久教授合影
后来我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没过多久又调到中国作协工作,与日本科同事们的来往就少了。那时黄华珍经被提拔为副科长,与徐前结婚,我们住在同一栋筒子楼,偶尔碰见,点点头,说几句话。我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时,经常在国内外出差,忙不过来,于是想起了文笔好的徐前,与她合作翻译了黑柳彻子的《窗边的阿彻》《从中学生到女演员》(原名为《彻子频道》),爱新觉罗•浩的《流浪王妃》,爱新觉罗•显琦的《清朝王女的一生》等。我主编日本作家立松和平的文集时,请她和黄华珍译了长篇小说《雷神鸟》……
徐前的译稿通达顺畅,但她是慢性子,只要“火没上房”,她是不着急的。有时,马上就到交稿期了,她负责的部分还没有弄完,我就吓唬她:到时候交不了,这本书能不能出,就难说了!她一听不仅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还可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急了,就把自己闷在屋子里,三天三夜,靠吃牛肉干喝开水,把稿子弄得干干净净交上来。与她合作,我摸到了门道:她身体好,能吃苦,敢拼搏,到了交稿期,不用着急,只要稍加“恐吓威胁”,肯定齐活,她有这个本事。
她和黄华珍到日本留学,相继取得二松学舍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我问过黄华珍,你二十几岁就当了副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怎么突然想起留学来了?他说:“我在印尼没上大学就回国参加工作了,随着形势的发展、职务的变化,越来越觉得知识贫乏,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于是就想到日本攻读国际贸易,学点本事。原计划学习几年就回去,没承想,念书念上了瘾,兴趣也发生了变化,老师看我坐得住,爱读书,认定我是做学问的料,建议我学书志学(涵盖文献、版本和目录等学科)。这门学问虽然枯燥,却是百学之基础,与中日文化交流也有密切关系,我很感兴趣,就留了下来,主修中国哲学,梳理古文献,考察中国思想史,主要靠奖学金维持学习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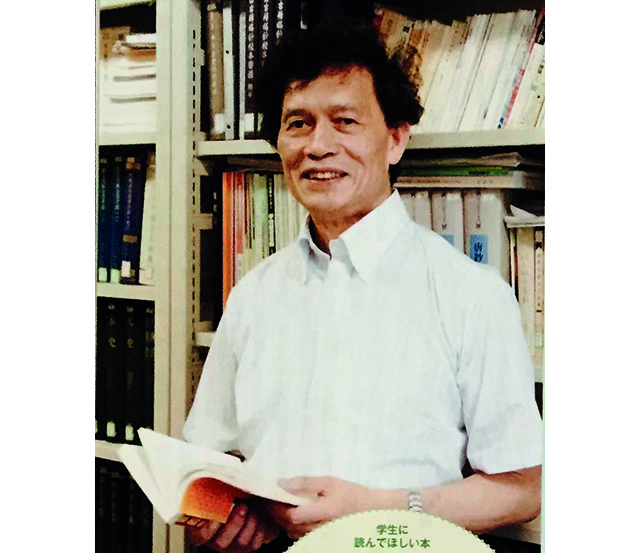
黄华珍在大学研究室

徐前在大学教员室
书志学是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在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真伪优劣,刊误纠谬,避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而这需要丰富深厚的古文、古籍的修养,但黄华珍从小在海外长大,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完全是靠着废寝忘食地刻苦钻研,才步入堂奥的。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一边在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当教授,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和日本相继出版了《日藏宋本庄子音义》《庄子音义研究》《日藏汉籍研究——以宋元版为中心》《日本奈良与兴福寺藏两种古钞本研究》等十余本学术专著,同时还担任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会长,编辑出版会报、会刊,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日学术会议上,经常看到他来去匆匆的身影。退休后,他仍然热衷于书志学研究,将他的发现、考证、思考、学养融入一篇篇论文中。
徐前长期在日本大学法学部、国士馆大学法学部教汉语,兼搞翻译,出版了学术专著《漱石与子规的汉诗》和多种日语汉语研修教材。二松学舍大学前校长石川忠久在为其专著写的序言中说:“作者徐前与夫君黄华珍共同来日本,在二松学舍大学院学习,靠萤雪之功,双双获得博士学位,是对令人羡慕的鸳鸯夫妻。”这几年,她又钟情律诗汉俳创作,在上班的路上,在归家的途中,在夕阳和落樱中,捕捉诗意,咏叹人生,时有新作在朋友圈流传,在日本的报刊发表。我不懂音韵,不敢置喙,但听方家说,她严格遵守格律,写意、写景、书事,雍容不迫,潇洒闲适,颇有功力。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细想起来,黄华珍和徐前在为人处世、脾气秉性、生活情趣等方面,确实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一是聪明智慧。黄华珍在研究宋代刻本时,发现《庄子音义》,他以此为契机展开研究,一本本专著喷涌而出。徐前在研究夏目漱石和正冈子规的汉诗的过程中,学会了音律,于是开始写律诗。二是真诚厚道。他们讲话办事,一是一二是二,绝无假大空。接人待物,慷慨大方,热情周到。三是缜密。他们的论文,条分缕析,环环相扣,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他们在生活中,诸如在出国留学、攻读学位、选择职业、赡养父母,置业买房等重要的人生节点上,也是脚踏实地,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明智而稳妥,所以朋友们说他们是“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戏称其家为“四合堂”: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珠联璧合,天作之合。
他们的人缘好,朋友多,古道热肠。例如我每次单独到日本访问,他们都热心帮忙。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生来愚钝,方向感极差,近乎不辨方向(日语叫方向音痴),他们常常为我当向导,有时甚至抽空陪我去实地考察采访。平素有什么疑难问题,不管何时何地,一个微信过去,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查阅资料文献,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黄华珍和徐前出版的学术专著
他们的新家,我去过几次,不仅宽敞明亮,满堂书香,而且环境优美,鸟语花香,是个做学问、过日子的好地方。而且我发现,徐前的学问和厨艺共同成长。以前她最拿手的红烧大虾、冰糖肘子、糖醋排骨、香辣蟹之类的菜肴,为适应人们口味的变化,也与时俱进,在吸收日本、西方及东南亚菜肴精华的基础上,重新组合排列,焕然一新,自成一家,再配上优雅餐具,色香味形俱佳。最近听说她又推出传统的英式下午茶,可惜尚无机会品尝,不敢妄评。
他们久居海外,为生活工作奔忙,但却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上。不仅订阅中文报刊,还年年回国探亲访友、旅行观光。他们对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了如指掌,有时比我知道的还多、还周详。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恨所爱,憧憬和希望,甚至牢骚和遗憾,几乎与我们完全一样。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从小在日本长大的儿子,为了不忘祖国的语言,自己立了个规矩,回家不讲日语,甚至父母与中国客人偶讲几句日语,他都有意见。在外面,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总是主动告诉周围的人我是中国人,并为此而自豪。然而,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公司,他非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可能是他的真诚、坦率,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一个在山川异域成长的青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自重?我想,可能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前几天徐前告诉我,她已经开始教授孙辈汉语,每周一次,目的是让他们从小就记住自己的根。
他们在异国他乡辛辛苦苦几十年,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教书,传播中华文明,讲述中国故事,不知把多少学子领进了中国文化的大门?
如今,他们已经年近古稀,但流淌在血脉中的对故国家园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切切之意,不但没有被岁月稀释,反而更加强烈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