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大,真理的味道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石库门开始成为上海独具特色的里弄住宅,成为一道别具一格的东方风景,可谓老上海的一个缩影。四通八达的弄堂里,旅馆、作坊、报馆,也都会来占用一方天地;小食摊、修鞋匠、理发师傅、算命先生,以及穿街走巷的各种露天职业者,都来此谋求营生。川流不息的移民,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行当,上演着老上海的市井百态,成为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最浪漫、最能触动人心的风景。
老渔阳里2号是老革命党人柏文蔚的公馆,是一幢典型的一楼一底石库门房子,高高门楣上方是一个A字三角形石雕。楼上楼下,布局精巧,整洁干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陈独秀住进来后,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馆一下子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住进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就开始筹划《新青年》“劳动节专号”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标志着《新青年》在离开上海两年多后又回到了上海,同时也表明新文化运动的“旗舰”——《新青年》阵营面临着分裂。对陈独秀的离开,胡适回忆说:“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
胡适说得没错,陈独秀在上海交上了新朋友。作为思想界的明星,前来拜访陈独秀的人络绎不绝。这个时候,老渔阳里 2 号的座上宾主要是《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以及李达、施存统、陈公培、沈雁冰、俞秀松等社交名流或青年骄子。他们大多数跟陈独秀一样,都曾留学日本,会讲日文,且都研读过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了这样的共同语言,这群青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兴致盎然。老渔阳里2号不仅成了他们聚会的中心,而且陈独秀还与这些“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开始了筹划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
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之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孙中山还与其他六位广州军政府总裁致电北京政府:“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宜为平情处置,庶服天下之人心”。国民党支持五四运动,但并不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中回忆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代表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就暴露了国民党不走群众路线的致命缺点,“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在这样的情势和局面下,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邵力子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建立政党,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尽管经过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中译本依然没有。
陈独秀在和“新朋友”们的交谈中,不禁感叹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我们必须加快翻译出版工作的步伐。”
陈独秀的感叹,也是大家的共识,于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
李汉俊说:“搞文化运动,也必须要搞好粮食供给,我们确实应该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的书籍最要紧。”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开山之作,也是公认的经典著作,且篇幅简短,翻译出版相对比较容易一些。经过讨论,大家确定首先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为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1848年1月,他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著述;2月18日至19日,在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共23页的以德文单行本印刷的小册子,装帧十分简陋,仅印刷几百册,作为内部资料发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不公开销售。但是,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那一年,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170多年来,这部伟大著作一直放射着真理的光芒,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战士,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现在,由谁来把《共产党宣言》完整翻译出来呢?
这时,邵力子告诉陈独秀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浙江义乌的陈参一莫属。”
邵力子还告诉陈独秀,陈参一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四大金刚”之一,“一师风潮”的风云人物。“一师风潮”的直接起因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效仿北京大学《新潮》杂志,创办了《浙江新潮》。
1919年10月2日,杭州举行“祭孔”大典。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下,新潮社的学生首先表示不参加。学生傅彬然、施存统等在孔子诞生日赴西湖烟霞洞附近拜谒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之墓以示反叛。校长经亨颐对学生的态度表示支持,并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借口到山西太原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提前离开了杭州,避而不就“丁祭典礼”陪祭官。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施存统写此文的动机是“出于其父异常虐待其母,而他自己难乎为子:顺父逆母,不孝;帮母斗父,亦不孝。然则如之何而后乎?于是深入一步思维,认识到这个矛盾,是由于中国的旧伦理观念根本不对头,乃联想到一种新学说了”。施存统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相信“要改造社会,的确非先从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非孝》一经刊发,引起浙江当局的高度紧张,再联系到此前学生不参加“祭孔”的行为,便视为洪水猛兽,扣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并归罪于校长经亨颐,勒令开除传播新文化的“四大金刚”——新派国文教员陈参一、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浙江当局指责陈参一等人“系不学无术之辈,弃文言而不授,全用白话,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将使全校师生堕入魔障”。反动当局还出动警察包围了学校,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
陈参一1891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农民家庭,小伙伴们都叫他“融融哥”,曾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回祖国。6月,他受聘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
陈独秀说:“那好,赶紧把选本找好,寄给他尽快翻译出来。”
邵力子说:“现在我们手头上既没有《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也没有英文版,而且我们懂德文的人也比较少。我看,还是从日译本中找一个最好的译本翻译为好。”
李汉俊转过头来问戴季陶:“我看到1月份《星期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你翻译的《马克思传》,译得很好。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版本?”
“我翻译的这篇《马克思传》是我在日本留学时带回来的日译本,作者是威廉·李卜克内西,日文译者叫志津野又郎,刊登在 1906 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戴季陶想了想说:“不过,我记得,在这一期杂志上还刊登了主编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日译本是完整的译本。那时候,日本马克思主义十分盛行,但唯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准公开刊行。这本《社会主义研究》是以‘学术研究资料’的名义内部发行而公之于众的。1909年,我回国时偷偷带回来了一册。”
“好,就用你收藏的这个版本。”陈独秀又转过头来问邵力子:“现在参一在哪里?”
“听说现在还在杭州。”邵力子说。
“季陶,你赶紧用快信把《共产党宣言》寄给他,写一封信,请他尽快翻译,完成后直接来上海。”陈独秀吩咐道。
“好。我正好想邀请他来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戴季陶十分高兴地说:“我现在就回去办理,以《星期评论》的名义向他约稿。翻译好了,我们立即连载发表。”
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都表示赞成,大家高高兴兴地结束了座谈,仿佛完成了一件压在心头多年的大事儿一样。

陈望道(1891-1977年),浙江义乌人,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
1920年2月,陈参一收到约稿信,当即承诺下来,并作出一个决定,带着《共产党宣言》回老家义乌,进行翻译工作。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暂时躲开城市的喧嚣,绕开“一师风潮”的烦心干扰,专心专意完成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曾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早就想着有机会翻译出来,没想到现在机会找上门来了,那感觉就像是“天上掉下了一个林妹妹”。
吹面不寒杨柳风。早春三月,万物复苏。陈参一回到了这个名叫分水塘村的小山村。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家,就是母亲。
回到了家,就是回到了避风港。因为“一师风潮”丢了工作,慈祥的母亲没有责怪他,只有安慰,只有慈爱。与母亲寒暄之后,陈参一请母亲帮他把家中久未修葺的柴房收拾干净,他要选一个僻静的角落,安安静静地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母亲二话不说,一边答应着,一边帮儿子收拾。
两张长凳,架上一块木板,一盏煤油灯,既当书桌,又当床铺。一间简陋的书房就这样完成了。
山区的春天,乍暖还寒。小小的柴房里,昏黄的灯光闪烁。日日夜夜,陈参一或伏案奋笔疾书,或字斟句酌沉思冥想。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全身心投入到翻译的工作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
这一天,母亲给儿子送来了亲手裹的粽子,外加一碟红糖。
过了一阵子,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一些?”
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
又过了一阵子,母亲进屋来收拾碗筷,看见儿子的嘴巴乌黑乌黑的,很是奇怪,走上前仔细一瞧,才发现竟然是满嘴的墨汁,一碟红糖却放在那里一点儿没动。原来,儿子是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
此情此景,母亲看了,又疼又爱,故意笑着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
儿子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地说:“甜,真甜。”
这时,母亲起身拿过来一面镜子,递给儿子,有些埋怨地说:“你这个书呆子,墨汁也是甜的呀?你瞧瞧你的嘴,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儿子这才明白过来。母子俩都笑了。笑声萦绕在柴房的每一个角落,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温馨。
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正因为这种无法言喻的精神之甘、真理之味,无数的革命先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
于是就有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的时候,陈参一将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陈望道——追望大道,表明自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一年,陈望道 29 岁。
信仰的味道是甜的。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个人为什么要坚定信仰?因为他需要始终不渝地用真理开启人生的密码。
一个人为什么要坚守真理?因为他需要始终如一地用信仰指明人生的方向。
《共产党宣言》全文只有两万字,但陈望道却费了平时翻译的五倍功夫,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成。
1920 年 4 月,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如约前往上海。邵力子、戴季陶带着他来到老渔阳里 2 号,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喜过望,赏识有加。文稿经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基本定稿。
然而,事不凑巧,这个时候,因上海当局实施邮检,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共产党宣言》连载的计划落空了。恰在这时,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了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建党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的事情。维经斯基听说后,当即决定资助出版。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正式诞生了,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这本用白报纸印刷的56页的小册子,长18 厘米,宽12厘米,比小32开略小。每页11行,每行36字,5号繁体字竖排印刷,新式标点符号断句,侧面书眉印有“共产党宣言”字样。封面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封面署名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图书定价“大洋一角”,初版印数为1000 册。略显遗憾的是,由于排版疏忽,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不过,在1920年9月再版时,作了修订,再印1000册,封面也由红色改成了蓝色。
阅读全书可以看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意译的方法为主,在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中,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处,均用英文原文加括号的形式作了注释。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的标题旁边,除了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作了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据此,有史料说,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曾请陈独秀出面,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对照进行了翻译完善。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 17 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后,陈望道通过周作人寄给鲁迅一册。鲁迅先生阅读后,称赞道:“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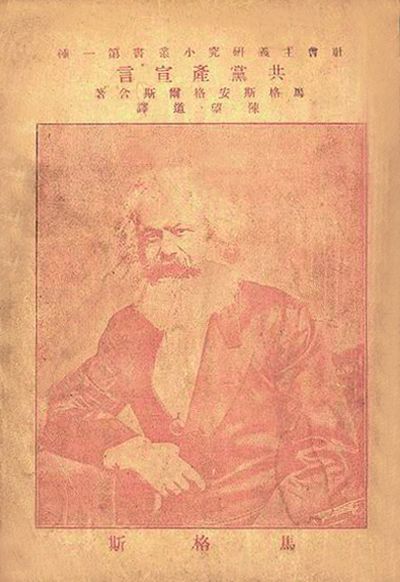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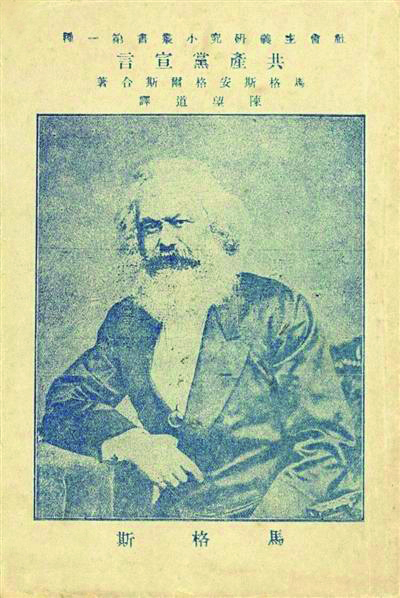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第二版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接受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1920 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 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除了《共产党宣言》外,在这个时期,陈独秀先后指导并要求他的同人和追随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有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陈望道翻译和介绍的《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传播真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把《新青年》的编辑事务委托陈望道主持办理,一方面考虑到“望道境遇不佳”,一方面确实对其能力水平特别信任和赞赏。同时,茅盾、李达、李汉俊也加入了编辑部工作。陈望道主持编辑出版工作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